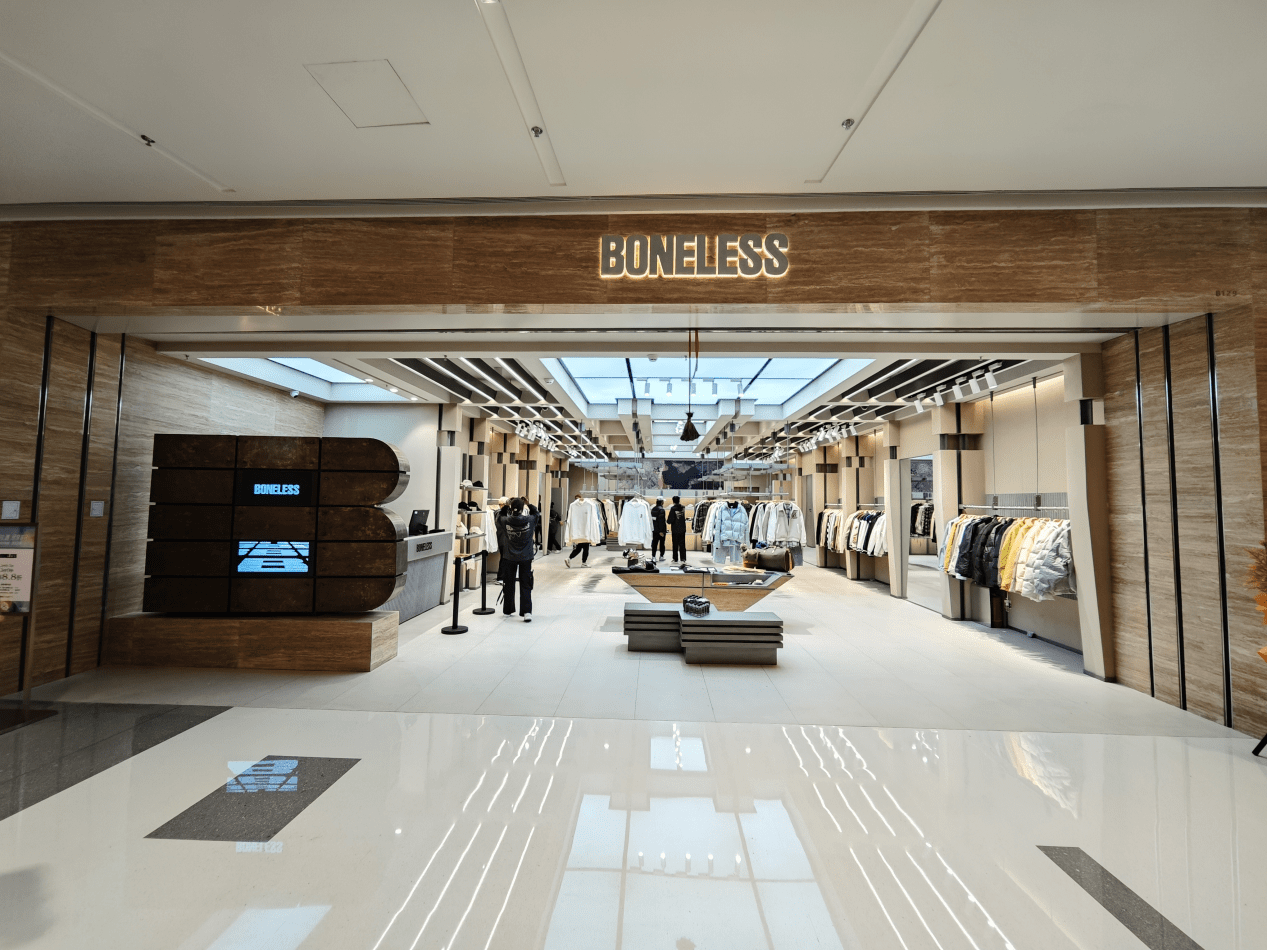鄭州童裝精品尾貨批發
東莞市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1-2月份,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4.6%,其中出口下降10.8%,單月數據罕見地沒有列出。
無獨有偶,中國海關總署也合并了2020年1、2月份的進出口數值,以美元計,中國進出口總額下降11%,其中出口下降17.2%。
業務幾近休克的外貿商們,做好了豁出去的準備,一群中老年老板轉向直播、微商等平臺,玩命清庫存。但內銷似乎也沒那么容易,內外擠壓下,這群人還要面臨低端產業向東南亞加速轉型的陣痛。
寧波外貿老板趙科的主業是做LED燈。不過前一陣子他從河南老家四處搜羅民用口罩產能,并下了個1000萬口罩的訂單。
“我沒準備做口罩。”趙科趕緊澄清,他的一個大客戶是加拿大規模零售商,疫情期間對方沒有直接停掉合作,只是減少了燈具訂單量,但同時請求他幫忙尋找口罩貨源。
這讓他有點悲喜交加。為了維護疫情期間變得極為脆弱的客戶關系,他必須費盡心力地“不務正業”,且不會從這筆訂單中賺錢。
2月中旬,國內疫情爆發,趙科在老家過年都沒過好,因為國外客戶奪命連環call,催著加急生產。
好不容易復工,國外疫情又嚴重起來,“國外門店都關了,新產品不需要,加上客戶倉庫爆滿,老產品也不讓發貨了。”他愁得天天喝茶去火。
3月5日后,隨著外貿訂單大面積取消,趙科不得不把已生產的貨壓到自己倉庫。客戶提貨時間拖后近一個月,這意味著往年給85%尾款的時間也順延一個月,資金周轉壓力更大。
趙科的訂單中,有70%來自俄羅斯。盡管當地疫情并不嚴重,但仍有九成訂單被取消。原來疫情導致全球石油用量下降,石油大國俄羅斯首先受到沖擊——盧布大幅貶值,一度跌下18%左右。
而外貿通常以美元結算,俄羅斯客戶的采購成本一下子增加近20個點,但產品利潤平時只有十幾個點。在這種情況下,不做生意就是賺到,就像那些沒在3月殺入股市的投資者一樣,不出手就是贏家。
趙科預計5月中旬會有大批外貿工廠倒閉,“其實不只是LED行業,所有的外貿行業都很慘,除了醫療器械。”他發現同行現在做的全是年前訂單,大部分在4月底結束,好一點的可能撐到5月初。他長期接觸的一位供應商,正常情況下,一年營收可以做到八千萬美元,結果今年一季度只接到200萬美元的訂單,僅有去年的1/40。
生存擠壓之下,為爭奪有限的訂單,價格戰又死灰復燃。“以前這個行業可能有15個點的利潤,現在至少會砍掉5個點,報出歷史最低價。”可趙科觀察發現,價格戰效果有限,客戶仍然不下訂單。

“2019年已經很慘了,沒想到2020年還更慘。”他抿了口茶,半天才咽下去。原本他打算趁今年扭轉局勢,擴大招聘、推廣智能新產品,沒想到遭遇疫情黑天鵝。
如今工廠每個月支出40多萬元,他準備在4月底裁掉三分之一員工。“撐一兩個月還好,三個月就很難,如果5月疫情能控制住,還有盼頭。”
寧波的外貿服裝老板唐小鳳,心里更苦,她經營寧波飛創進出口有限公司(Ningbo Future Import & Export Co.Ltd)。服裝出口去年就陷入低迷。
根據海關數據,2019年中國出口服裝及衣著附件1513.676億美元,同比下降4.0%。唐小鳳的工廠只做歐美時尚款,分為Forever21等商場品牌和沃爾瑪等超市品牌兩種,其中99.5%銷往美國。
3月15日是關鍵節點。當時美國各州大多宣布“居家令”,鼓勵民眾在4月20日前減少出門。由于貨運儲運期加上柜期需要45天,4月20日前商店有足夠庫存銷售,所以5月30日前上架的訂單被紛紛取消,幅度達50%以上。
往年4月前后的換季時期,是全年最忙的生產旺季。但今年工廠很清閑,被取消的訂單緊急停止生產。但唐小鳳還有一批成品衣,在太平洋的貨輪上飄著——由于客戶倉庫關閉,到岸后需要自己找倉庫存放。
3月、4月都在虧損。她現在對每一個經營數據“門兒清”:“已經被取消了100萬件訂單,貨值800萬元左右,預計全年利潤減少幾百萬元,降幅達50%左右。”
外貿服裝業損失巨大,也與商品屬性有關: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時裝設計款,過了時節就不再流行,不像一支筆、一盞燈,疫情之后還能原價銷售。唐小鳳決定按1-2折處理庫存,如果這批春裝囤一年再賣,除了支付一大筆倉儲費外,過季衣服也很難賣出原價。
一線城市的消費者可能已經在門店和奧特萊斯見識了品牌清庫存的決心。在北京一家賽特奧萊,阿迪、耐克以五折、六折甩賣,撿白菜的消費者排起長隊,門店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而另一品牌ONLY,則80元一件甩賣積壓的襯衣、裙裝。
在廣州慶豐服裝城等批發檔口,大量外貿衣服在甩庫存,有網友發現,“一件質量良好的迪士尼T恤批發價只有6元,童裝T恤5元,不少堆地上的衣服只有一兩元。”
疫情讓外貿幾乎進入休克狀態。在出口外貿業占主導的義烏和廣州,商家受損情況更為嚴重。多位受訪人士表示,義烏商品城的鋪子很多在轉租。按規定商戶必須每天開門,于是不少老板免費轉讓門店給別人做生意,就當幫忙開個門。
驊威文化創始人郭祥彬以玩具產業起家,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2013年仍在發酵的歐債危機,他說道,“以往危機中起碼能出貨,頂多是利潤降低,而這次危機直接出不了貨,等于無收入。”
唐小鳳透露,哪怕在中美貿易摩擦期間,服裝行業直到2019年11月才增加7.5%的關稅,中國供應商調整價格后,利潤空間雖然降低,但去年訂單并不算少,“以前只要有貨出去就有成交,但這次損失是致命的。疫情拖得越晚,風險越大。”
如果從宏觀數據來看,外貿沖擊的范疇或許超乎企業主層面的想象。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出口國,2019年中國全年出口17.23萬億元。僅在2019年10月舉辦的第126屆廣交會上,到會境外采購商18.6萬人,當月中國出口成交額超過2000億元。但今年春季廣交會剛宣布延期到6月,且會場搬到線上。部分外貿廠商對線上的效果心懷忐忑。

中國民營企業可能是韌性最強的一類經濟體。沒有老板甘愿坐以待斃。很多人為了自救,比羅永浩更早出現在“帶貨”平臺上。
義烏商貿老板萬豪云透露,不久前商城集團組織店鋪對接網紅,借助直播賣貨。“現在進店客人翻倍,但接單不到去年的三分之一。因為進店的一個個小年輕兒,很多都是做自媒體的,他們到店里不是買貨,主要是找素材拍視頻。但老板們聽說能幫忙帶貨,都熱情不得了,以前不存在這種情況。”
電商平臺活躍在轉內銷的浪潮中,比如阿里在“春雷計劃2020”里公布資源支持、減免費用等措施,京東旗下社交電商“京喜”上線“工廠價賣光外貿貨”專場,拼多多甚至與寧波政府戰略合作,推動超1.5萬家外貿企業轉內需市場。
萬豪云發現,商家們清理外貿庫存相當于“半賣半送”,比如電器處理價格,只有外貿出貨價的一半。大商戶們也放下了對規模的執著——以往外貿單一般是上萬件起送,而現在國內客人拿三五件,他們也愿意出貨。
這導致義烏外貿市場出現兩重天現象。萬豪云告訴我們,義烏的商貿城主要做銷往歐美的市場貨,這次受沖擊很大;但其他處理尾貨的庫存市場反而熱鬧起來,一方面市場上的庫存貨變多,另一方面國內很多失去工作的人轉向擺地攤謀生,他們主要銷售庫存尾貨——而義烏市場在該領域優勢明顯。
萬豪云的朋友李愛騰,一個貨拉拉司機,也兼職做起來電商直播。這名年輕人的危機感很強,外貿慘淡直接影響他的運輸生意,有時兩天都接不到一個單子,一次“蹲了一天搶到一個單,加上油費和車損總共才收到80元”。但他不想消沉下去,便盤算著利用商家清庫存轉內銷的機會賺錢。
李愛騰白天去市場拿貨,晚上擺好三腳架直播賣貨,頭兩天居然賣了70件玩具,有一兩百人在抖音觀看。但他很快發現效果不佳,決定從規則流程開始改進,“要搞明白售后、打單、物流交接,然后再補充20-30個品類,玩具更適合節慶日,還是應該主打當下能用到的日用品。”

不過外貿轉內銷真的順暢嗎?經驗豐富的萬豪云看出其中端倪:即使低價,他也不敢放開拿貨。“產品不對路,以電器為例,有些外貿產品沒有售后顧慮,所以質量參差不齊;而國內有售后,所以不敢賣差貨。”他和商家商定,拿外貿貨的前提是必須保證售后服務。
一名深圳制衣廠老板“沃克MAN”,連續在今日頭條發布賣貨短視頻,稱“外貿訂單只能持續到6月,每天無所事事浪費時間,分享荷葉連衣裙”,但底下評論只有寥寥兩條。他還吐槽遇到奇葩,一名買家收貨后,300元尾款對方死活不給,微信也不回。
趙科則發現,LED行業的國內市場已被大寡頭壟斷,很難再切進去。如果進行線上交易,幾乎是從零學起,他覺得這兩條路都不可行,便決定“先歇著,保存實力,等疫情結束”。
對于占外貿出口較大的服裝行業來說,外貿與內銷的差異更大。唐小鳳在4月初上線微店和直播平臺,最近在考慮開淘寶店處理外貿庫存,“還在摸索中,如果效果好,以后我們會多加一條內銷線。”但有一點讓她很“頭疼”——內銷的款式傾向韓國風格、偏甜美小巧;而自家的外貿貨都是歐美系,設計簡單隨意、尺碼也有局限。
最大的問題則在于一時無法轉變思維方式,“外貿貨最少2000件起訂,而內銷很多是一兩件、一兩百件,工人的抵觸心理比較大。因為工資按件計,規模效應沒起來的話,收入也會相差很大。我們十年來一直做外貿,對內銷市場真不了解。”
量品CEO虞黎達創業前,在阿瑪尼、Burberry等品牌服裝代工廠干了近20年。在接受采訪時,他直言:“外貿轉內銷根本不現實,其實我們業內認為,整個2020年國內的服裝業會非常困難。”
虞黎達觀察到,春裝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上市后,受疫情影響已經砸在品牌手里。他發現很多品牌的春裝賣不出去后,經銷商會以“品質不太好”等為由,拒絕再履行合約,或者延遲收貨,導致部分夏裝也出不去。而內銷的秋冬服裝訂貨會一般在二三月開,現在看疫情估計要推遲到五六月,加上采購原料輔料的時間,今年初冬也來不及上貨。
“內貿日子就不好過,外貿企業何必再轉內銷?轉了還沒客戶,尺寸也有問題,因為都是按訂單做,不是做庫存。”他覺得應對這種外貿“休克”只有一招——停工。
殘酷之處在于,這也意味著大量工人失業或降薪。有網友就反映,表妹一家年后從湖南老家回到惠州鞋廠,本來以為歇工兩個月,出去有活干就可以賺錢,沒想到去了沒事做,一家四口在外面開銷還大。他們已經考慮回老家,“起碼有口飯吃”。

疫情在全球蔓延,有的工廠停工不久就能復產,有的卻永遠消失了。在疫情的放大鏡下,中國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的進程也按下前進鍵。
48歲的中年男人冷楓很早就有覺察,十幾年來,他做工的東莞東昌鞋業相繼關閉湖南、廣州的工廠,轉去越南建廠房。2019年,東莞總部的工廠也在縮小,從三層樓廠房和三層樓宿舍,縮減到一樓一個門面房和二樓廠房,其他空間租給18家小企業。
他之前聽內部消息說,今年5月中國工廠將全部撤向越南,但東莞廠的116名員工沒想到,疫情還沒結束,老板就決定提早撤離。
冷楓透露,工廠主要生產網布鞋和靴子,外貿訂單占七八成。2月17日復工后沒有訂單,只能做年前接的外包活。其中,財務、報關、倉庫的20名員工上了一個月班,打鞋底和抽鞋面兩個部門上了一周班,剩下的工人因為沒活干,一直沒去工廠。
3月16日,所有工人停止上班,19日工廠關閉,期間廠里資產評估66萬元,給工人發了2月工資。冷楓和工友們不滿的是,他們沒有一分錢裁員補償,而以前湖南和廣州工廠撤退的時候,都還有這筆費用。
“我們有六七十個人,在這里干了十幾年,現在四五十歲了,出去也很難找到工作,很多工廠有年齡限制,改行去五金廠、電子廠,我們也吃不消。”一個多月下來,冷楓還沒找到合適的工作,他仍在東莞等待勞動仲裁,同時尋找工作機會,有些工友則回了老家。
冷楓對老板的舉措并不意外。“越南每個月的工人工資一千多元,中國是四五千元。”事實上,在中國設廠的服裝、鞋帽、家具等產業很早就向越南轉移,高科技制造業也在陸續轉移,比如英特爾多年前就在胡志明市設立全球最大的封測廠,三星也于2019年10月關閉在中國的最后一家手機工廠。
歷史學家施展調研發現,越南的優勢在于勞動力和稅收政策上,而在工廠租金、水電費上處于劣勢。另外,越南沒有完整的重工業基礎(原料和零部件需從中國等進口),沒有廣闊的內需市場(制造業產品多出口),導致轉移產業多是對供應鏈需求低、人工成本占比高的組裝工序,而其對零部件復雜處理的前段環節跟不上,相應的制造業很難轉移。
今年3月初,當中國的疫情影響到蘋果供應鏈,蘋果高管層仍拒絕下屬提議的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到越南的措施,甚至也叫停了在印度開設iPhone 11的計劃鄭州童裝精品尾貨批發,因為當地沒準備好熟練的勞動力或蘋果期望的強大基礎設施。為此蘋果繼續選擇在中國生產。
這與疫情加劇東昌鞋業等的產業轉移并不矛盾,換句話說,疫情讓企業更深刻認識到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如果該產業更看重勞動力成本,那就轉移到更便宜的東南亞,如果對工人熟練程度或其他設施要求高,那仍有望留在中國。
唐小鳳將中國扮演世界工廠的優勢歸結為“文化”。“中國人對賺錢有很強的欲望和沖動,不像東南亞工人動不動就罷工或偷懶。”她所在時裝行業生產周期三個月,有時需要加班趕工,國內工人更適應生產節奏。“如果做基礎款,一年四季都能賣,就適合開在東南亞,另外花式面料等流行的特殊面料也需要在國內做,因為國外的設備技術不成熟。”

在虞黎達看來,高附加值的、要求快速反應的會留在中國,因為這種對工藝要求高,對價格不敏感,規模也較小;轉到越南等地的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組裝。
但他也很憂心越南的情況,“從加入WTO開始,中國的代加工制造業經歷了15年左右的黃金期,也是出口外貿業拼勞動力、拼成本的紅利期,但我覺得越南最多有5年,因為人口基數比中國少,未來拼這些肯定不行,得拼研發、效率和速度。”
施展提出的核心觀點是,制造業從中國向越南轉移并不是“轉走”,而是中國供應鏈網絡的一種“溢出”,也就是說越南很難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施展在2019年完成調研,沒想到在新書上市的2020年1月,一場疫情“黑天鵝”能成為產業溢出的催化劑。

西姆股權激勵研究院:我們專注于公司股權戰略、股權激勵(含員工持股計劃)、國企改革的研究、咨詢、培訓和方案設計。咨詢熱線: